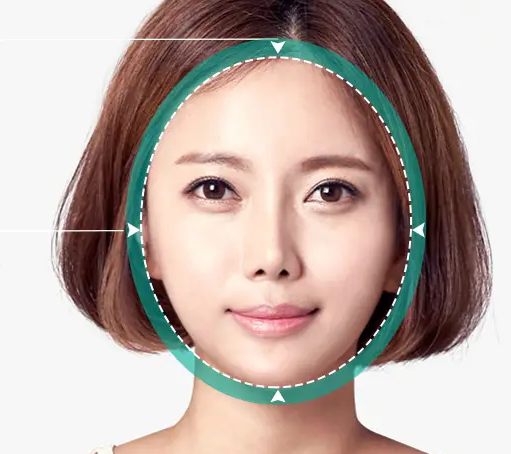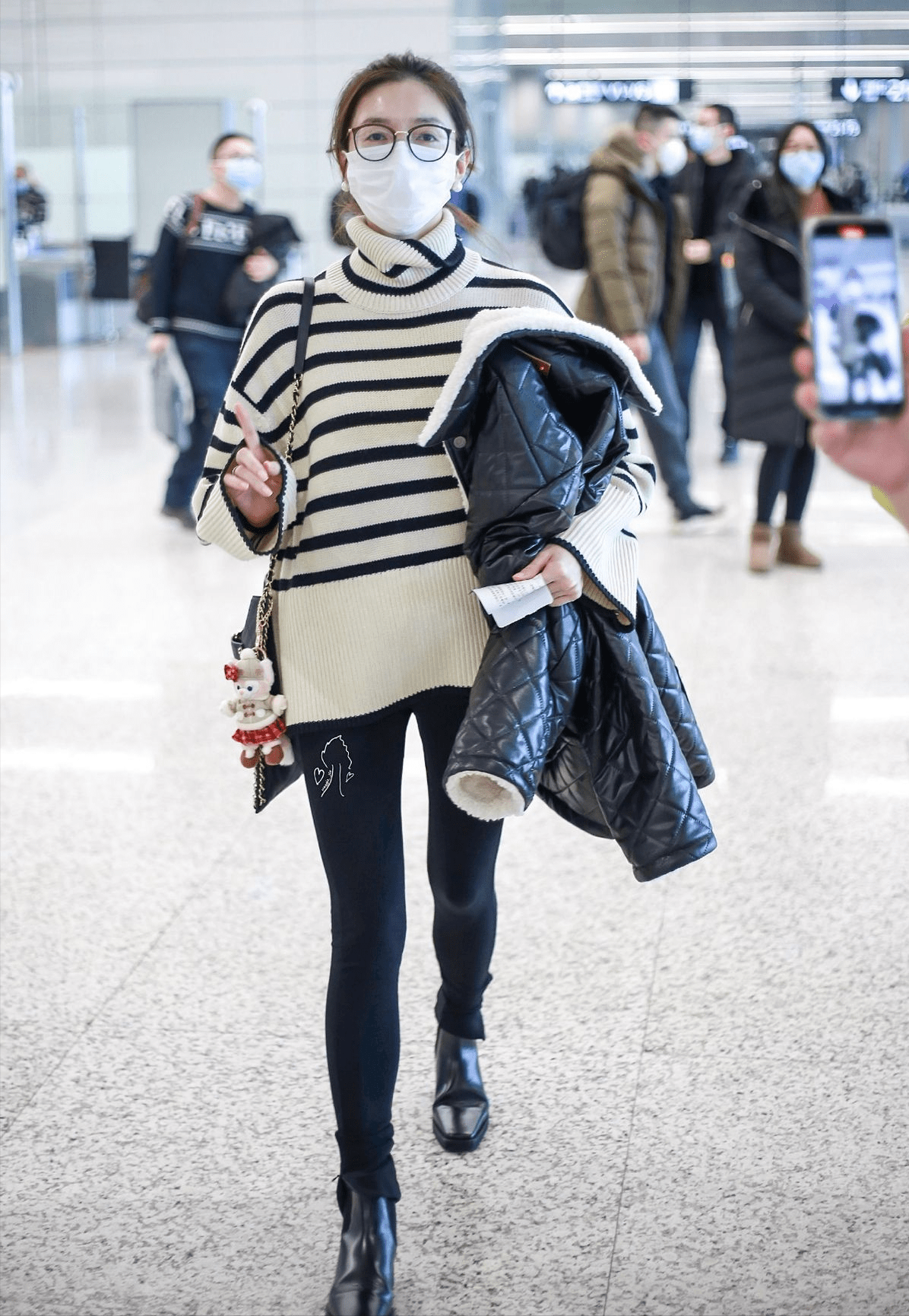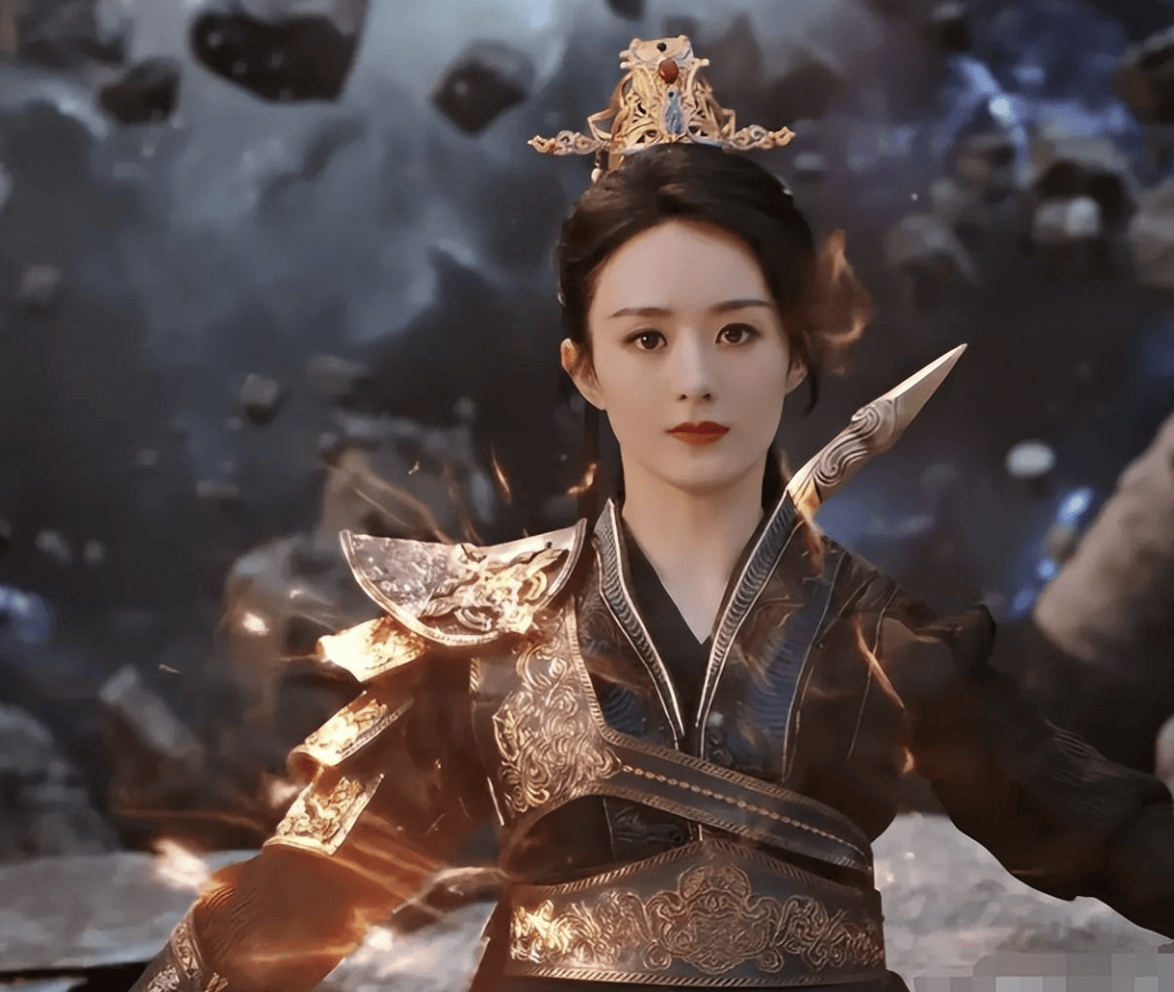贾樟柯
之前他总是通过电影将别人的故事给大家,这一次,请他一起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。
我这几年住在老家,山西汾阳贾家庄。回到家乡之后,我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轻松了很多。我是一个县城里出生、长大的人,我最初的作品、我看世界的角度肯定都是县城的角度。比如说,我们接收到的信息都是经过了几道的过滤或者传递,我们不处于中心位置,就像沈从文先生说的“边城”,文化的边缘、经济的边缘、政治的边缘。所以,边缘的角度、边城的角度是我独特的一个角度。后来,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,那个角度逐渐丧失了,但是我的思维习惯又是那个角度。当我这五六年回到了家乡之后,我觉得我回到了自己,我很舒服,有一种抽身事外的感觉。
很多在北京会在意的事情,在家乡一点儿都不在意;在北京一点儿不在意的事情,在家乡会很在意。在北京占据我们大部分时间的,是关于社会的、行业的各种大量的信息,包括人和人之间的竞争,大家都是以事业为中心。回了家乡,我们都是自然人,事业不重要,能活就行。我们所有人都有事业,但也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没什么事业,说来说去的那些事儿,我们在老家的饭桌上一句都不提。
我看安东尼奥尼的一部电影特有感触,一开场,主人公住院,他对他的妈妈说:我现在熟人很多,亲人很少。这就是我在北京的感受,熟人很多,每天见各种各样的人,但是亲人很少。回到老家,见一个就是亲人,都是从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。我们更接近人的本源,我们在一起会谈家庭、谈情感、谈很私人的话题,城市里需要的社交距离这里都没有。
回到家乡之后,我想拍一部纪录片来讲述农村经验和农村记忆。我们需要了解乡村,因为我们整个国家是从农业社会过来的,这个社会存在的很多问题、困惑我们的很多现象,和农村的生活习惯、道德塑造是有关联的。我们很多人的父母辈从农村出来,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农村经验,但我们要理解我们的父母辈、理解这个社会,确实需要一些农村经验。
刚好我们贾家庄一直有很强的文学传统,五六十年代,几位“山药蛋派作家”马烽、西戎、孙谦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,当时他们已经是部级的领导了,辞了官,回乡写作,就住在贾家庄。同时,在中国的文学史上,乡村经验、乡村题材是一个始终没有中断的线索,一代一代的作家都在感受乡村和乡村生活。我就觉得,把乡村和文学结合到一起是一个很好的角度。
于是,我以马烽、贾平凹、余华、梁鸿四位作家为主线,拍摄了纪录片《一直游到海水变蓝》。这四位作家成名之前都是农民或者小城市居民,他们长期关注农村也长期书写农村。借由文学家超强的感悟能力和讲述能力,我们的纪录片可以更有效率地展现农村的变迁。四位作家从不同的角度讲了很多的农村经验、农村生活和农村记忆,连接起来就是这七十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的一张蓝图。在这些年里,农村的变化是空前的,比如青壮年的流失导致农村空心化、老龄化,当然农村也有很大程度的现代化。
贾樟柯 | 巨变与不变
贾樟柯
很有趣的是,在当代社会,人们在精神上越来越多地谈论乡村,身体却在越来越往城市中去,形成了一个自我的逆流。我非常理解,因为乡村资源非常匮乏,同样是人的一辈子,为什么非要在一个资源缺乏的地方生活呢?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,所以我也不会去浪漫化乡村。
纪录片吸引我的就是它的未知性。拍剧情片我们有很多预知,大概知道应该拍些什么、拍成什么样子,但是拍纪录片只能有大致的预测。我们去拍一个人,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,但是他敞开心灵到什么程度、具体会讲些什么,真的不知道。我们去拍一个空间,在那个空间里会发生什么,也没有人知道。在那一瞬间,每个人都会接受崭新的信息,然后就有了两个问题——拍什么?怎么拍?这是真正地拍电影,在拍摄的一刹那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刚过去的2020年,我的工作计划因为疫情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原定要拍的电影和要演的电影都延期了。本来程耳导演的《不浪漫》要在去年正月开机,摄影棚都订好了,我出演,演完我就准备在清明节左右开始自己的电影《在清朝》 的搭景工作。疫情一来,全都不能开工了,这一年我就只好用来写剧本、拍短片。
经历了疫情,人们对家庭的重要性的理解又加强了。大家都知道家庭重要,但是平时忘了。我们和同事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要长,我在外景地、工作场景待的时间比在家里待的时间要长,迎来送往的朋友占据的时间比陪伴家人要长。我们往往对外来的朋友、合作伙伴、客户耗费了更多的时间、精力和注意力,觉得家人就是自己人,所以对他们有很多的疏忽和怠慢。
疫情让大家和家人朝夕相处,回归到真正的家庭生活,和家人之间的联系更紧密。疫情毕竟是一个危机嘛,我们发现,当危机来临的时候,跟我们站在一起的还是家人。于是我们反思过去对于家庭的疏忽,特别是男性,女性可能好很多,男性更多的还是社会动物,投放在家庭的关注力确实太少了。
贾樟柯 | 巨变与不变
贾樟柯
在疫情以前,我总是忙到该睡觉的时候才回家,哪里还有时间陪家人啊!疫情期间,我经常在家陪我妈看电视,我妈爱看谍战剧,我就陪着她把《潜伏》《风声》《北平无战事》这几部剧反复看。我还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:每天中午回家吃饭,尽量不在外面吃饭,也尽量不叫外卖。之前我每天上午工作、下午见朋友,现在频率没那么高了,可能一星期见一次朋友。
疫情让我确定了我是一个汾阳人,或者说我是一个生活在北京的汾阳人。在内心深处,过去的我没觉得自己属于任何一个城市,因为我在北京的时间很少,在家乡的时间也很少,我的生活和工作中总有大量的旅行,无论是珠海、广州、香港、巴黎还是纽约,我都有固定住的酒店、固定的朋友圈、几十年不变都要去的餐厅,这一套生活方法是完整的。但是疫情让我们收缩在自己最根据地的区域,一年多的时间里,哪里也去不了,很多人因而获得了地方性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地方性,但过去我们太忙碌了,没有意识到。我现在天天在北京,对我居住的街道、居委会都挺熟,之前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不存在的,疫情前我家周围的超市我从来没去过,疫情之后我天天去,我有了买菜、买水果的时间和机会,有了生活半径。
我拍了一部四分钟的短片《来访》,表达我在疫情期间的一些感受。我一直保持着拍短片的习惯,如果说拍电影是一种自我表达的话,只拍长片的自我表达的频率就太低了,因为长片电影的周期非常漫长。我算是比较稳定,两年拍一部长片,那两年也就表达一次。拍短片可以增加表达的频次,哪怕拍个两三分钟的短片,也可以把内心的小感受讲一讲,我很享受这个。其实短片是最活泼的电影形式,它有很多的可能性,它是最自由的形态。
我拍电影,更重要的是想留下一个真实的生存感受。这件事、这个人代表着我的一个生存感受,我想把这种生存感受表现出来、讲述出来。这种生存感受是从个体出发的,但它具有这个社会和时代的印记,因为我就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。